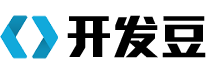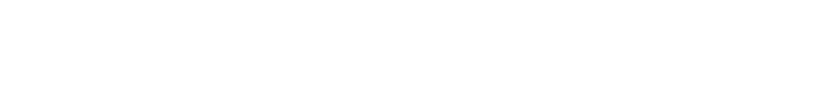
但他像一个电影哲学家
刘青云谈《暗花》及其他
潘:潘国灵,刘:刘青云
访问日期:2006年1月17日,地点:半岛酒店The Bar
潘:韦家辉的电影世界观很突出,命运、宿命、很黑色的,你在参与他的电影演出时,如何融入这个世界?你怎样看他这个世界?
刘:和韦先生的合作,先不谈电视合作的部分,首先他给我的印象并不象一个编剧或导演,反而像一个哲学家。他给我的印象是圈中很少有的,虽然他的学历不太高,但他是一个很有学识、思考能力很强、很有原则与要求的人,他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去看一个灰色的世界。
《暗花》海报
潘:既是灰色,又是乐观?
刘:他是很乐观的,我不知道这个乐观态度是他的本质还是他的思考模式,我觉得他看这个世界是灰的,但他以很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面对,他的心理素质很好。
潘:《暗花》这电影的角色造型很突出,你剃光头,身穿豹纹衣服,角色造型的表现性很强,对你来说,当时是否一个新尝试?
刘:是的,我很喜欢Bruce(余家安)对服装的看法,《暗花》(1998)的衫裤鞋袜看似普通,但当时时装的trend是很top line的,那对球鞋我听闻就是他收藏多年的私伙,市面上没得卖的。这个造型给了我很多启发去演这个角色,我觉得演员的造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当你穿了一件衣服,装扮完后,你觉得自己便是这个角色,与你的感觉很吻合,相反有时候你做了造型,但对角色仍然没有头绪。《暗花》中,我剪了头发,穿上衣服,自然便与他的行为吻合起来。
潘:即使这个造型可以帮到你,也要靠演员掌握,你当时如何揣摩角色?
刘:当时所有东西都很模糊,《暗花》一直到拍的时候,没有人知道剧情,杜先生、韦先生在《暗花》开始了这种拍法,这对电影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启示,我们不知在干什么,我们只有一个很模糊的剧情,而每样东西每天都在不停改变,我们去到澳门,想了很多东西,都没办法串联起整个故事脉络,只有一些很概括的想法,然后韦先生、杜先生就拍一些我们觉得应该有的场合,不断拍、拍、拍,最后就是由导演重新剪辑,连贯起整个故事。
潘:造型也包括道具,你那个弹球就很有趣,尤其在你被拘留的那场戏,配合光线效果非常突出。
刘:我是到最后才发现袋中有一个球,而差不多去到最后一场才知道我的袋中有个人头。
《暗花》中的刘青云
潘:这很有趣,在电影中,你一出场就坐在巴士上,把弹球运于手指之间,但演员却是到最后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球。
刘:后期才加上去的。他给我一个球,我在想给我一个球我可以做什么,我又不懂耍杂技,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了,到底要利用那个球来做什么。《暗花》给我的特别经验是,很多东西都是不能预知的,没有东西可以掌握在手中,这样反而没有任何负担,让我觉得电影原来可以怎样拍都行。原本有一场戏是说伟仔被人打死的,而且已经拍完了,但拍着拍着,大家的思维又改变了,你可以看到整部电影其实没什么故事性的,只有事件,而事件的表达不一定要发展出一条line来,只是一件事、一件事、独立的个案、独立的场口,最后就由导演连贯起来,旗帜这个故事是很跳的,不是一个很叙述式的故事,形式上与其他电影很不同。
这种拍法令我想象,这个角色是怎样的呢?这个角色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,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不知道他的身份、能力,只能在形象上去了解他,例如他的背景。他流露的东西很少,这令人可以发挥很大的想象力,可能会觉得他很能打,或者他受过特别训练,对枪械有认识,因为以前可能是军人,因此想象空间很大,我很少演出空间容量如此大的电影。
潘:不是一般的拍法。
刘:对呀,也不是很有章法的那一种,例如坐牢那一场戏,设计了那样的灯光,大家就用手将厕纸撕成碎片,剧情一直发展,到了狱中那场,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个「宝仔」也是洪生的人,这个事前我也不知道,一切都是即时发生的。
潘:你参与的电影中有很多双雄格局,如《暗花》中你和梁朝伟,《真心英雄》(1998)中你和黎明,《暗战》(1999)中你和刘德华,《暗战2》(2001)中你和郑伊健,另外又有很多群戏,两者在演出上有分别吗?
刘:其实分别并不在于两个人还是一群人,最重要始终是你怎样去建立自己的角色。当然有时你会因为对手而改变自己的演法,但有时chemistry这东西是很奇妙的,很难去安排两人一起便一定好看,你和某些人站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作用。例如《暗战》,我和刘德华拍了几场戏,之后我去了看rough cut,已令人觉得这两人间好象会发生一些事情,会吸引我们看下去。当时甚至是未有剧情的,只有几个镜头,但已令人觉得挺好看,某些演员搞在一起便会有这样的chemistry。
《真心英雄》DVD封面
潘:说起角色造型,除了《暗花》,《真心英雄》也非常突出,你头戴牛仔帽,留了胡子。
刘:那又是Bruce做的。Bruce经常和我说一个笑话,他说《真心英雄》给我一些很cheap的衣服,但我穿得挺好看。(潘:有一点像牛仔)对呀!我很喜欢那个角色,他是黑帮世界中的一个明星,所有东西都要顶级的,但其实他有点老套,他不是深思熟虑得那么厉害,没有star的头脑,最重要是做出来好看,有型一点。我经常觉得他会希望自己死于枪战,也一定要被人看到——秋哥被人打了很多枪,之后他仍可以打死几个,最后是抽雪茄,抽着抽着就死了,有人仍说他还没有死,他希望自己是一个legend。如果他是一个legend,他更加接受不了自己跛了腿、做乞丐,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,他能够维持的原因就是他要报仇,这个人物在惨剧中有很大的改变。
潘:但有趣的是,他的死没有人知道,独自在天台上,被苍蝇围绕着,就这样死去了,这与他想象中的传奇之死分别很大。
刘:对,人就是这么悲哀。我挺喜欢的一点是,他第一次在天台上被人发觉,成功逃脱,但他重新回到同样的地方,又处于同样的位置。和大家讨论的时候,重点放在他应怎样死,就是又被人发觉,后来被人抛下街去。我说这个ending不太切合这个角色,他的生存能量是为了报仇,这是一件简单的事,最遗憾的就是做不到,最遗憾的是那个人在同样位置再出现一次,他只要「擝鸡」就可以了,他出现了,但等不及,死了,非常无奈,我觉得作为一个枭雄,这个处理会比较合适,命运就是这样。
潘:最末一场你演一个活死人,死了还能拿枪杀人,这难不难演?
刘:那一场不难演,只是难构思,我和乃海坐在一起构想,很苦恼,怎样可以人死了还能开枪。我记得拍这场戏那天是14号,三天后我就结婚了,我拍完那场戏,就搭了四点钟飞机由泰国回香港。这场戏有很多玻璃爆破,我第一次理解到——我们不是经常看到男主角中了枪之后仍要赶去教堂吗?我以前觉得这样做不客观也不理智,应该是先去医院,不去医院也先打个电话告诉她你中了枪,她一定不会怪你的,原来不是的,原来是你会先去教堂,对她说自己中了枪,解释自己不是不想结婚,只是中了两枪。我对乃海说,无论如何都要送我搭飞机,因为拍爆玻璃是有危险的,万一出了事的话。
潘:有什么角色你很想试的?
刘:其实很多角色我都未试过,但很多角色都不会找我演。我经常想做一个指挥家,或者一个吸毒、戒毒、吸毒、戒毒、最后信了神的人,这些角色我觉得都很好玩,但有何好看呢?很多时候其实不在乎角色,而是怎样去处理那个角色,很简单的也可以与众不同,视乎怎样去写,去发挥,并不需要一个很不同、很突出的角色。很多演员觉得演一个妓女很考演技,我不觉得,最重要是怎样写她,写她做些什么,些她是怎样的人,这些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自己的空间还不够大,我的思想空间还是太小,演员是从自我出发的,自我出发是一件很困惑的事,你是一个怎样的人,你的角色很难脱离这个影子。就算不是你本人,你对某些事的想法会影响你怎样处理一个角色,大家对喜怒哀乐的看法都不同,我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不同,那我的看法就变成我演戏的特质,那就变成我,这就很容易变成一个限制,所有好处和坏处都矛盾的纠缠在一起,难以分辨。
本文收录于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《银河映像,难以想象》一书
作者: 潘国灵 主编
出版社: 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出品方: 世纪文景
副标题: 韦家辉+杜琪峰+创作兵团
创作不易,感谢支持